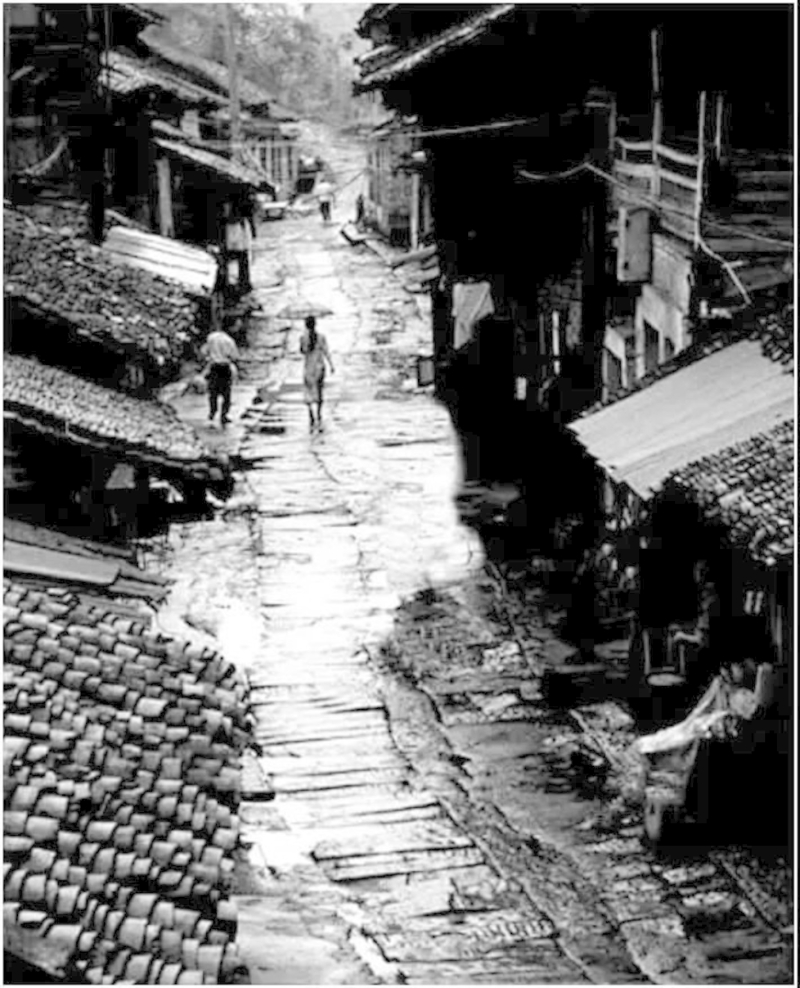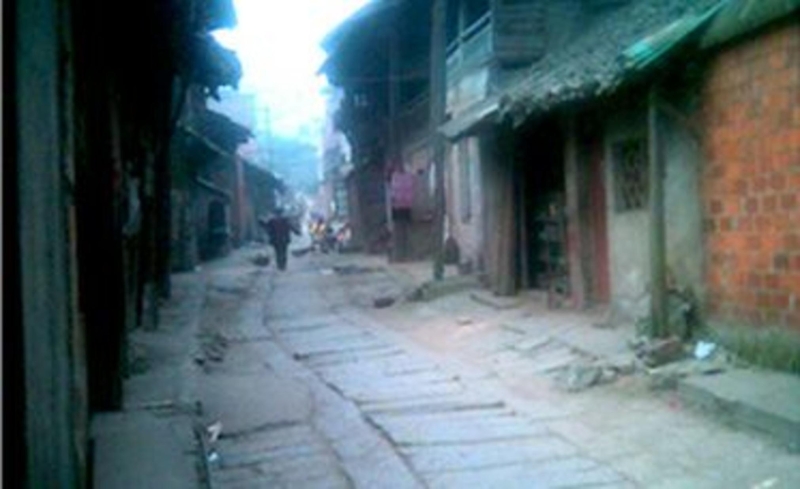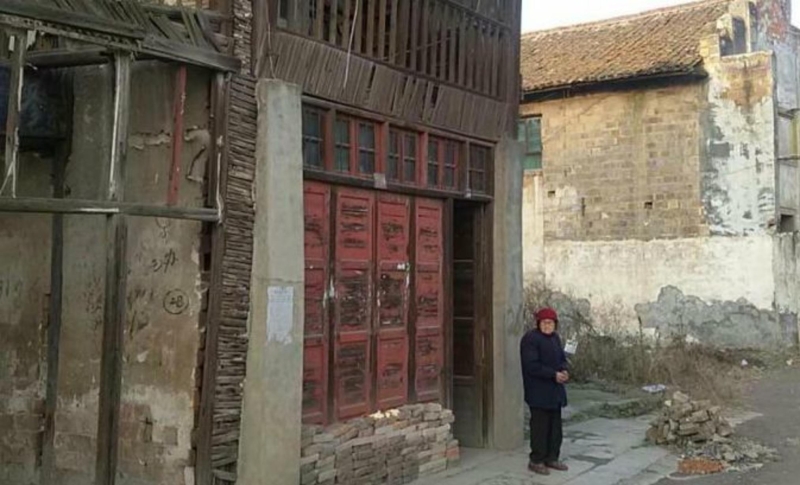Òõ¢¡╩ð│Ã─¤ú¼ËðÊ╗ùl╔¯▓ÏÁ─ðí¢Íú¼╩Ã├±ç°│§─Û¢¿Á─íúÊ‗¤ÓîªË┌¡é║■µé(zh¿¿n)└¤¢Íú¼╦²Á─├¹ÎÍ▒Ò¢ðð┬¢ÍíúÙmÄÎÂ╚À▒╚A╦ãÕ\ú¼Ê▓ÄÎÂ╚´L┤ÁËÛäâú¼Üv¢ø(j¿®ng)£µ╔ú¥ÌÎâ║¾ú¼ð┬╠ÊÊ▓ôQ┴╦┼fÀ¹ú¼Á½╚╦éâÊ╗Í▒í░ð┬¢Íí▒í░ð┬¢Íí▒ÁÏ¢ðÍ°ú¼Ê╗░┘ÂÓ─ÛÂ╝▓╗È°©─┐┌íú
ÈÆıf╣Ô¥w─ÛÚgú¼Òõ¢¡┐h┴¯Êè¥│â╚(n¿¿i)Á─Â┤═Ñ║■╦«├µú¼┬Ò┬ÂÁ─║■ͦ╚ıØu´@ÂÓú¼▒Ò¢M┐ù├±▒èç·║■╠¯ÍÌíóÈý╠´¢¿╬¦ãüÝíúÈ┌┐h│Ã─¤▓┐ú¼┘Y╦«àR╚ÙÂ┤═Ñ╠Äú¼ËðÊ╗╠ý╚╗║■×│ú¼¢ð¶ö?sh¿┤)Ê║■ú¼▒¥╩ÃüÝ═¨┤¼▓░Á─▒▄´L©█ú¼▀@Ê╗À¼ç·║■┼dÍÌ║¾ú¼┤¾Á╠╔¤▀Ç¢¿┴╦Ê╗Ψ╬Õ├ÎÚLÁ─┬Ú╩»ÿ‗ú¼╠ý╚╗┴╝©█Ê▓¥═│╔┴╦Òõ¢¡Î¯ƒß¶[Á─╔╠ÿI(y¿¿)┤a¯^íú
¶ö?sh¿┤)Ê║■ËÊ░ÂËðÊ╗Ψí░´w°P╔¢í▒ú¼Ê‗╔¢│╔ÙuÎýá¯ú¼└¤░┘ðı▒Òîó▀@└´¢ð│╔┴╦í░Ùu╣½Îýí▒íú╣Ô¥wÂ■╩«Â■─Ûú¼╝┤╣½È¬1896─Ûú¼┐h©«¥═È┌▀@Îý╔¤¢¿┴╦Ê╗Ψ║å┬¬Á─ƒo¥Ç═¿ð┼┼_ú¼┤╬─Û▀@â║▒Ò│╔┴╦Òõ¢¡┐hίÈþÁ─Ùèê¾¥Ííú
1903─Ûú¼Ê╗éÇ¢ð┘R°Ö┘eÁ─╗¨Â¢¢╠═¢ú¼È┌ÙxÙu╣½Îý─¤â╔└´╠ÄÁ─╣┼│Ã╠┴ú¼╝┤¼F(xi¿ñn)È┌Á─¡é║■┤u═▀ÅS╠Äú¼¢¿┴╦Ê╗Ψ╠ý͸¢╠╠├íú╠┴ÊÈ╣┼│Ã├³├¹ú¼─╦Ê‗Üv╩À╔¤▀@└´┤_ËðÊ╗Ψ╣┼│Ã│Ïíú
ô■(j¿┤)ÃÕ╝╬æcíÂÒõ¢¡┐hÍ¥íÀËø¦dú¼╚²ç°òrã┌ú¼ıÐ┴ÊÁ█äóéõÐ▓Êò╬õ┴ÛíóÚL╔│íó╣┴ÍÁ╚ÁÏú¼Êè┤╦ÁÏ▒▒═¿È└Ûûú¼─¤ÿO×t¤µú¼Ö{Ö®┴Í┴óú¼╔╠┘Z╦ãÈãú¼╩Ã╠ÄÍÏʬÁ─æ(zh¿ñn)┬Èÿð╝~ú¼▒ÒÍ■═┴ç·│Ãú¼¢¿│╔┴╦Òõ¢¡Î¯ÈþÁ─│Ã│Ïí¬í¬ıÐ┴Ê╣┼│Ãíú╣┼│Ã×ÚÒõ¢¡░╦¥░Í«Ê╗ú¼Ë┌├¸┤·▒╗ÅUíú╔¤╩└╝o¥┼╩«─Û┤·─®ú¼ð┬¢Í¥Ë├±ÊÎÁ┬▄èÈ┌À┐╬¦©─Èýòrú¼▀Ç═┌│÷┴╦«ö─ÛÁ─│Ãëª┤uíú
├±ç°│§─Ûú¼┐h©«×Ú═Ïı╣Òõ¢¡┐h│Ãú¼░▓Í├═ÔüÝ¢ø(j¿®ng)╔╠ı▀ú¼øQ¿È┌Ùu╣½Îý┼c╣┼│Ã╠┴Í«Úg¢¿Ê╗ùlâ╔└´ÚL¢Íú¼╚í├¹×Úí░ð┬¢Íí▒íú¢ÍÁ└Ë╔┬Ú╩»║═ÃÓ╩»░ÕÕeÛÉõü¥═ú¼À┐╬¦║═õü├µ┤¾Â╝╩Ãͱ─¥¢Yÿïú¼╬¦░ñ╬¦íóõü▀Bõüú¼ð┬¢Í┼c┐h│áé║■µé(zh¿¿n)͸¢Í¤Ó▀Bíú
├±ç°│§─Ûú¼Òõ¢¡┐hÈOÍ├╩«▒úú¼▒ú¤┬ÈO╝Îú¼┐h│Ãî┘╩ð▒úú¼¦á┴¨╝ÎíúÍ┴├±ÚgÂ■╩«ã▀─Ûú¼╝┤1938─Ûú¼îìððÓl(xi¿íng)ú¿µé(zh¿¿n)ú®▒ú╝ÎÍãú¼ð┬¢ÍäØ×Ú╣┼│õé(zh¿¿n)ú¼┤╬─Û┼c¡é║■µé(zh¿¿n)║¤▓óíú
1912─Ûú¼└^Ùèê¾¥Í║¾ú¼╣┼│Ã╠┴▀àËÍ¢¿ã┴╦Òõ¢¡┐hç°├±Á┌╬Õ╦¢┴óðíîWú¿¢±├Ì┬Ú╣½╦¥â╚(n¿¿i)ú®íú║¾░ß▀wÍ┴¶ö?sh¿┤)Ê║■ξ░Âíú¢ËÍ°ú¼ÄÎéÇÞF¢│║═ÞTÈýă©ÁÈ┌Ùu╣½ÎýÌkã┴╦Ê╗éÇí░ȼ═¼║═ÞTÈýÅSí▒ú¼Ú_╩╝┴╦║åå╬Á─ÖCðÁÍãÈýíú
«öòrÁ─Ùu╣½Îý▀Ç╩ÃéÇð╠ê÷íú1927─Ûú¼Á┌Ê╗┤╬┤¾©´├³╩ºöíú¼Òõ¢¡©´├³┴Ê╩┐▓╠¢▄íóðýÍ▓─¤íóäó╬õíóÛÉ╬─æcÁ╚ú¼¥═▒╗ç°├±³hÜó║ªË┌┤╦íú╣▓«a(ch¿ún)³h¥═╩Ãæ{¢ÕÈþã┌Ìr(n¿«ng)├±▀\äËÁ─Ë░Ýæú¼æ{¢Õ¯É╦ãÒõ¢¡Ëó┴ÊÁ─ú░┘╚f©´├³┴Ê╩┐Á─§rЬú¼ð┬├±©´├³▓┼Á├ÊÈ│╔╣ªúí
1937─Ûú¼╩Î┤╬└¡═¿Òõʵ╣½┬Àòrú¼È┌Ùu╣½Îý▀ÇÈO┴╦Ê╗éÇ▄çı¥íúð┬¢ÍÊ╗òr│╔┴╦Òõ¢¡Á─À▒╚AÍ«ÁÏíú
1944─Û4È┬ú¼ÃÍ╚A╚ıÖCÌZı¿Òõ¢¡ú¼┼c├└┐ı▄èÈ«╚AÁ─´w╗óÛá╝ñæ(zh¿ñn)íúÒõ¢¡│Ã─¤ÈÔÍÏäô(chu¿ñng)ú¼ØM─┐»ÅÛíú═¼─Û6È┬4╚ıú¼╚ı▄è▀MÀ©Òõ¢¡┐h│Ãú¼±vÈ·Ë┌ð┬¢Ííóð┬Òõ┤ÕÊ╗ĺú¿¢±î┘ð┬┼d╔þà^(q¿▒)ú®íú¼F(xi¿ñn)─Û░╦╩«╚²ÜqÁ─Í▄ðÒËó└¤╚╦È°ËHÐ█─┐Â├┴╦╚ı▒¥╣ÝÎËÁ─ÀNÀN▒®ððíú
└¤╚╦ıfú¼╚ı▄èı╝¯Ið┬¢Í║¾ú¼È┌¢Í║¾ðÌ¢¿┴╦áIÀ┐íóÅù╦ÄÄýíó╣├─´ÿÃú¿╬┐░▓╦¨ú®íó▓┘ê÷Á╚ú¼┤¾╦┴ƒ²Üóô´┬Ëú¼ÎÑ▓ÂïD┼«│õ«ö╬┐░▓ïDú¼ð┬¢ÍÈSÂÓ╔╠╝Ê¥═┤╦╠ËÙx┴╦Òõ¢¡íú
╚ı▒¥═¢Á║¾ú¼ð┬¢ÍÚ_╩╝ÍÏ¢¿íúð┬¢Í▓╗▀hÁ─±R╣½õüËðÊ╗ðı┬ÖÁ─┤¾æ¶ú¼Ê‗Î┌ý¶│úÈÔ╗×─ú¼¢ø(j¿®ng)´L╦«¤╚╔·³cô▄ú¼ý¶╠├ʬÐÏ╦«Â°Í■ú¼Ë┌╩Ãú¼┬Ö╝ÊÈ┌¶ö?sh¿┤)Ê║■ξ░¢¿Í├┴╦ð┬Á─┬Ö╝ÊÎ┌ý¶íúÅ─┤╦ú¼┬Öðı▀@éÇ┤¾╝ÊÎÕ¥═È┌ð┬¢Í©¢¢³Í├ÁÏ¢¿À┐ú¼ð¦B(y¿úng)╔·¤óíú
È┌┬Ö╝ÊÁ─Ë░Ýæ¤┬ú¼Ê╗¢ð╬──¤ËóÁ─┬Ú╔╠ú¼Ð¹╝»Òõ¢¡▓┐À¦╔╠╝ÊÈ┌┬Ö╝ÊÎ┌ý¶┼ÈÚ_ÈO┴╦í░Òõ¢¡Â╦╠®¤Ú┬Úððí▒ú¼┬Úðð¤┬¦á╩«╚²╝Êõü├µú¼È┌ð┬¢Íð╬│╔┴╦│§¥▀ÊÄ(gu¿®)─úÁ─├Ìíó┬ÚõN╩█Ê╗ùl¢Ííú
Ë╔┤╦ú¼ð┬¢ÍÁ─ÁÛõü▒Ò┤╬Á┌ÐË╔ýíú╣ÔÍ▄ðÒËó└¤╚╦ËøÁ├Á─¥═Ëðú║äó▒ú║═╦Äõüú¼ð▄╚f╠®íóð▄╚f┼d░┘Ïøõüú¼▓▄ÝÿËøíóÍtʵ¤Úíóäó╝¬╠®íóʵ║═¤ÚÁ╚─¤Ïøõüú¼▀ÇËð┬Öãı╔·íó═§Â¼╔·íó┬Ö¤ÒØMÁ╚ÂÓ╝Ê═└ÈÎððú¼┬Ö┼d╠®íó┬Ö▒ú╔·Á─Ë═ıÑÀ╗ú¼▓²╔²╩óÁ─ò°╝êõüú¼▓╠Ô¨├»Á─▒Ì┼┌õüú¼Íx╣ôÁ─ÙsÏøÁÛú¼È°ð┬ÿ‗¥ã╝Êú¼┼Ý╝Ê´£ÎËõüú¼┼Ý╝ÊÞFõüú¼═§Á┬║═├Îõüú¼┴ÝËð┐═ùúíó▓ÞÿÃíó┤║ÿÃíó┘Çê÷íóæ‗░Óíóë█ã¸Á╚íú┤╦═Ôú¼Ìr(n¿«ng)┘Q(m¿ño)╩ðê÷╔¤Á─╣╚íó├Îíó├Ìíó┬Úíó¢█íó▓Þíó╣Síó¶~Á╚¢╗ÊÎú¼Ê▓╩«ÀÍ╝t╗íú
║Ë─¤Á─í░ç└£µ║úí▒üÝ┴╦ú¼╔¢û|Á─í░┼ú░ÈðUí▒üÝ┴╦ú¼¢¡╬¸Á─í░È°╝¬▓²í▒üÝ┴╦ú¼îÄÓl(xi¿íng)Á─í░±R┤¾À╩í▒üÝ┴╦í¡í¡▀@ð®╔╠╠ûÁ─├¹ÀQÂ╝┤¾ÍÃ╚¶ËÌú¼┤¾Ð┼╚¶╦Îú¼║▄¢ËÁÏÜÔíú«ö─ÛÁ─ð┬¢ÍТú¼║åÍ▒À▒ÿsÁ├▓╗Á├┴╦íú░Î╠ý▄ç╦«±R²êú¼┤¿┴¸▓╗¤óú╗═Ý╔¤ƒ¶╗\©▀Æýú¼╣Ô▓╩ÛæÙxíú├┐«öÀÛ─Û▀^╣Ø(ji¿ª)ú¼üÝ▀@└´┘ÅÏøÁ─╚╦╠ÏäeÂÓú¼╩▓├┤¢ßÿú¿³S╗¿ú®íó╣┼È┬ú¿║·¢Àú®íó╔¢ıõ║ú╬Âíó╝t░Îã¼╠Ãú¼┤þ¢¢╗ÃðÁ╚©▒╩│ãÀ╩«ÀÍ╗▒¼íúÌr(n¿«ng)┘Q(m¿ño)╩ðê÷΢ÙuÎÑ°åú¼ÜóÏiÈÎÐ‗ú¼Ê╗┼╔À▒├ªíú©¸¥ãÁÛäØ╚¡ðð┴¯ú¼Ðþ´ïθÿÀú¼ƒß¶[ÀÃÀ▓íú
ð┬¢Í╔¤Á─╩ð├±Ð¢ú¼ËðÜg┬òðªıZú¼Ëð╦ß╠┐Ó└▒ú¼╚þ═¼╩ðê÷╔¤Á─ı{(di¿ño)╬ÂãÀ╬Õ╬Â┴¨║═ú¼Ê╗欥Ò╚½íú░Î╠ý├ªË┌╔·ÊÔú¼Ê╗Á¢═Ý╔¤ú¼ËðÁ─Î▀¢Í┤«¤´ú¼ËðÁ─┬áæ‗│¬Ã·ú¼▓╗òrû|╝Ê▀ÇËð││╝▄┬òú¼╬¸╝Êé¸üÝí░¢ð┤▓í▒┬òú¼¤▓┼¡░ºÿÀú¼╚╦Úg▒»Ügú¼È┌▀@└´▒ݼF(xi¿ñn)Á├┴▄└ý▒MÍ┬íú
Í▄ðÒËó└¤╚╦ıfú¼«ö─ÛÊ╗├¹ðı╠ãÁ─└¤Á¨ú¼│ú─Û╦─╝¥╠ßÍ°éǤ҃ƒ╗@ÎËú¼┤®╦¾Ë┌ð┬¢ÍÍ«╔¤ú¼¢ð┘uí░¤ÒƒƒÐ¾╗╣╗¿╠Ãú¼Öë└ã╣¤ÎË┬Ú¤Ò©Ôí▒ú¼Ê╗Í╗ͱ╗@ÎËB(y¿úng)╗¯┴╦┴¨┐┌╚╦íú
▀ÇËðú¼í░È°ð┬ÿ‗¥ã╝Êí▒±Y├¹┐hâ╚(n¿¿i)═Ôú¼┼▄╠├Á─╗´Ëïò■▀║║╚ú¼╩▓├┤í░ßuÍ¡├µíó┼ú╚Ô├µú¼═Ô┤¯Ê╗éÇ├Ô┤a├µúíîÆË═├µú¼Â╝╝Ë┤aú¼▀Çʬ╝Ü├µÄºÐ©©╔ú¼═Ô╝ËÊ╗éÇ│┤Ïi©╬í▒ú¼┬áÁ├╚╦┐┌╦«Í▒┴¸íú«ö─ÛÒõ¢¡┐h│ÃËð╬╗í░├±ç°Èè╚╦í▒¢ð┬Ö┤¾Ëóú¼╩Ã▀@└´Á─│ú┐═ú¼╦¹×Ú▀@éÇ¥ã╝Êîæ▀^Ê╗╩ÎÈèú¼í░ͱ▀BùU╔¤´ï║═▄Äú¼╝ÐÙ╚├└¥ã░Ð▒K╠Ýíú│ÓÁÏ▀wÊãÂíë╬┐═ú¼ÎË¢¬³S┤Î░ζ~═Þí▒ú¼©³╩╣▀@¥ã╝Ê├¹┬ò▀h▓Ñíú
ÈèÍðÁ─í░Âíë╬í▒ú¼─╦┼cÁ╠░¤ӢË│╩í░Tí▒ÎÍð╬Á─▒úÎoÁ╠░ÂÁ─¢¿Í■íú«öòrÁ─ı■©«┐╔─▄╩Ã╣─ä¯├±▒èîóÀ┐ÎË¢¿Á¢Á╠░Â▀àú¼Ë┌┤¾┼d═┴─¥òrú¼Â°╩╣¥ã╝ÊÁ─╔·ÊÔ©±═Ô┼d┬í░╔úí
í░╬─╚²▓┼┐═ùúí▒Á─└¤░Õ─´©³ò■└¡┐═ú¼Í╗┬á╦²├┐╠ýÂ╝È┌ÚT▀à▀║║╚ú║í░ð┬▒╗©CÄ΃ß║═║═ú¼▓╗ʬ╬Ê└¤░Õ─´░Ð─Ò═¤ú¼┐═ÄÎ┐═ÄÎ─¬¤Ëùëú¼▀MÁ¢ÁÛ└´¥═╩Ã╬ÊÁ─ËH©þ©þí¡í¡í▒
ð┬¢Í▀ÇËðéÇ¢ðí░ÈS┤¾░¶í▒Á─ØhÎËú¼À‗ïDézĺͰÊ╗Ùpâ║┼«ú¼Å─û|─¤║■Á─╠J╚ö╩ÄüÝÁ¢▀@└´Î÷├Î╔·ÊÔú¼╔·ÊÔÙm║├ú¼¥═╩Ãâ║┼«Á─╗Ú╩┬┘M╔±íú▓╗▀^ί¢Kú¼â║ÎËÈSø_╠ý▀Ç╩Ã╚ó┴╦Ûû┴_¢Í╔¤Ú_├ÎÁÛÁ─¶ö└¤░Õ╝ÊÁ─ú¢ðí¢Ò¶öô¤Òú¼┼«â║ÈS┤║╣├ät╝Ì¢o┴╦╬ÕÂÀ┤ÕÁ─ù¯┴°ú¼Ë┌╩Ãâ╔éÇËH╝ÊÂ╝░ßÁ¢ð┬¢ÍüÝú¼╣▓═¼Ú_┴╦Ê╗éÇ┤¾├ÎÁÛíú
║¾üÝú¼ÈSø_╠ý═Ô╚Ñ«ö▒°┴╦ú¼ù¯┴°╚Ñ╔¤║ú░l(f¿í)Ïö┴╦íú╩ú¤┬┴╦└¤╚╦║═ô╔®íó┤║╣├íúô╔®íó┤║╣├▀@¿µ▓▒¥¥═╩Ãð┬¢ÍÁ─â╔Âõ¢╗¿ú¼ð┬╗ÚÐÓáûú¼▒¥Èô║═ð┬ÓO·¶WÅP─Ñ─Ïú¼┐╔â╔éÇ─ð╚╦Â╝═Ô│÷┴╦ú¼▀@¥═¢oð┬¢ÍÁ─╚╦éâ┴¶¤┬┴╦ÈSÂÓ¤Ù¤¾Á─┐ıÚgú¼Ê▓¢o┴╦─Ãð®░┘╩┬▓╗╠¢Á──ðÎËËð┴╦ðó¥┤╠├┐═Á─ÖCò■ú¼Ê╗éÇéÇáĤÓÁ¢├ÎÁÛüÝ┘I├Î┴╦í¡í¡Ê╗òrÛPË┌╦²ézÁ─╣╩╩┬ú¼öçÁ├ı¹ùlð┬¢Í¤─╠ýø÷╦¼╦¼ú¼Â¼╠ý┼»Ð¾Ð¾íú
È┌ç°├±³h¢y(t¿»ng)Í╬òrã┌ú¼ð┬¢ÍÊ▓òrËðÛÄÈãüÝÊuíúòr─Ûú¼Ê╗└¯ðıÓl(xi¿íng)ÚLüÝ╣õ¢Íú¼┐┤╔¤┴╦╔¢û|ØhÎË┼ú│■û|Á─└¤ã┼íú▀@┼«ÎËÙmıfÀÃâAç°âA│Ãú¼├└╚¶╠ý¤╔ú¼àsÊ▓╠ý╔·¹É┘|(zh¿¼)ú¼ï╔ãG╚þ╗¿íúȧ─╬░┘░Ò╠¶Â║ú¼Ãº░ÒʲıTú¼╚╦╝ÊÂ╝▓╗╚Ùý░ú¼▀@╬╗Ól(xi¿íng)ÚLø]À¿ú¼Í╗║├┤«═¿╣┘©«ú¼ÎÑÎí╦¹╔·ÊÔ╔¤Á─Ê╗³cåû¯}ú¼Ë¹îó┼ú└¤░Õåû╣┘╦¥íú╬┤┴¤┼ú╝ÊîÄÈ©│÷╔¤Ãº┤¾Ð¾ú¼Ê▓ø]Îî╦¹Á├│Ðíú║¾┼ú│■û|╚Ã▓╗ãÂÒÁ├ãú¼ÄºÍ°└¤ã┼║═║óÎËÙxÚ_┴╦▀@é¹ð─Í«ÁÏú¼╗Ï┴╦╔¢û|└¤╝Êíú
▀@└¯Ól(xi¿íng)ÚLÁ╣╩ÃËð³c─½╦«ú¼Êèͱ╗@┤‗╦«Ê╗ê÷┐ıú¼▒ÒîæÈèÊ╗╩Î┴─ÊÈÎÈ╬┐ú║í░▒▒╚Ñ╔¢û|ð─╬┤îÄú¼Ë±Ë░¥²ÙS▓╗¤¹╗ÛíúÁ½È©┤╦╚Ñ╚È╗ÏÀÁú¼Â¿À²×Ú┼½Î÷À┐ËHíúí▒Ê▓▓╗ͬ╩Ã──À¢├µÁ─▒ú├▄╬┤Î÷║├ú¼▀@╩ÎÈè║¾üÝ¥╣┴¸┬õÁ¢┴╦ð┬¢Íú¼¤±â║©ÞÊ╗ÿËú¼▀B╚²│▀═»ÎËÂ╝─▄│¬íú
▀ÇËð═ÔÁÏÊ╗╬╗äó═└æ¶ú¼┼▄Á¢ð┬¢Íí░═Áí▒äe╚╦Á─└¤ã┼ú¼às▓╗┴¤▒╗±vÈ·È┌ð┬¢ÍÁ─ç°├±³h6642▓┐Ûá╬║▀BÚLͬÁ└┴╦íú▀@Ã░╦▀BÚL▓╗ͬ¤Ù┴╦éÇ╩▓├┤ËïÍ\ú¼▀@╠ýĺ╔¤Ã┌äı▒°ú¼¥╣Èp┴╦╦¹░Ù▀àÏi╚Ôíú┐╔Í^═Áð╚▓╗│╔À┤╬g¶~ú¼┼¬Á├äó═└æ¶▓╗╦¼┴╦┤¾░Ù─Ûíú
¢¡╬¸üÝÁ─È°╝¬▓²▒¥╩Ãç°▄è╩┐▒°ú¼üÝÁ¢ð┬¢Í║¾ú¼¤╚╩ÃÎ÷³c┘I┘uú¼┐╣æ(zh¿ñn)òrú¼«ö╔¤┴╦═¶é╬ı■©«Á─¡é║■µé(zh¿¿n)¥S│Íò■ò■ÚLú¼ÖM┐þÊ╗ͺ±g║ðÿîú¼´L╣ÔÊ╗òrú¼Ê▓║ª╚╦▓╗╔┘íú¢ÔÀ┼║¾ú¼╚╦├±ı■©«¢o│÷┬Àú¼Îî╦¹í░┌s─_Ïií▒×Ú╔·ú¼═Ý╔¤▀Ç╝µ┤‗©³ú¼ÊÈÍ┬ð┬¢Í▒ÒÂÓ┴╦Ê╗¥õÛPË┌╦¹Á─Ýÿ┐┌┴´ú║í░È°╝¬▓²ú¼ðíØh╝Úú¼╚ı┌s─_ÏiÊ╣Ã├░íúí▒
ðíðíð┬¢ÍÊ▓Î▀│÷┴╦▓╗╔┘├¹╚╦Í¥╩┐íú
╣┼│Ã╠┴┴x▓Þ═ñ▀àú¿¢±ð┬┼d╔þà^(q¿▒)ðl(w¿¿i)╔·╩Ê┼Èú®ú¼ËðéÇ║¾╔·ÎË¢ðÅêÌr(n¿«ng)ú¼1894─Û│÷╔·ú¼╠Ïò■Îxò°ú¼║¾┴¶îWÀ¿ç°ú¼½@Á├┴╦Ìr(n¿«ng)ÿI(y¿¿)▓®╩┐îW╬╗ú¼╩ÃÍðç°Èþã┌Ìr(n¿«ng)îW╝Êú¼Í°├¹Á─├±Í¸╚╦╩┐ú¼àó╝Ë▀^í░╬Õ╦─▀\äËí▒ú¼▓ó┼cÛÉÐË─ÛíóÍ▄¸üÝÁ╚Ê╗ã¢M┐ù▀^í░╬ÕϪ▀\äËí▒ú¼×ÚÃÓ─ÛîW╔·Á─┐é¯IÛáíú║¾ËÍÈ┌ÅVͦÌr(n¿«ng)├±▀\äËÍv┴ò╦¨ú¼¢YÎR┴╦├½Ø╔û|íú¢ÔÀ┼║¾ú¼╩▄Á¢├½Í¸¤»¢ËÊèú¼▓ó╗Ñ═¿ò°ð┼íú═Ý─Û¤óÎÒ╣┼│Ã╠┴▀àíú
1935─Ûú¼ÅêÌr(n¿«ng)╗Ï╝Ê╩íËHòrú¼È°┼c─©ËHÊ╗ãÀN┴╦Ê╗┐├╣╗¿ÿõú¼║¾üÝú¼▀@┐├┤¾ÿõÈ┌╣┼│Ã╠┴▀à═ª░╬┴╦░ÙéÇ╩└╝oíú├┐─Û╣╗¿Ú_òrú¼¤ÒÊþ╦─À¢ú¼ð┬¢Í╚╦¤▓ÜgÈ┌▀@┐├ÿõ¤┬│╦ø÷ð¦¤óú¼ıä╣┼ıô¢±ú¼Ë┌╩Ãú¼Òõ¢¡▒ÒËð┴╦í░╣╗¿ÿõ¤┬í▒▀@éÇÁÏ├¹íú1963─Ûú¼ÅêÌr(n¿«ng)▓í╩┼ú¼ð┬¢ÍÁ─╚╦îó╦¹ÈßË┌╣╗¿ÿõ┼Èíú
©]░▓ÂÏú¼ÎÍ╔┘─¤ú¼1853─Û│÷╔·ú¼ÃÕ─®Ïò╔·íó¢╠ÍIú¼Ïôσ╠¶▀xͦ©«┐╝ÈçÍðÁ─│╔┐â║═Á┬ððâ×(y¿¡u)«Éı▀ú¼▓óıã╬─ÅR╝└ýÙíú║¾╗Ï╝ÊÓl(xi¿íng)ð┬¢Íú¼Í¸ÍvË┌¡é║■ò°È║ÂÓ─Ûíú╦¹─┐Â├Â┤═Ñ║■´L©▀└╦╝▒ú¼üÝ═¨┤¼Í╗òrËðâA©▓Á─╬úÙUú¼Ë┌╣Ô¥w╚²╩«Ê╗─Ûú¼┬ô(li¿ón)¢jÁÏÀ¢╩┐╝Ø│╔┴óí░╩Î╩┐ò■í▒ú¼×Ú╩Î─╝¥Þäô(chu¿ñng)¢¿í░Â┤═Ñ¥╚╔·┴xÂ╔í▒ú¼Èý┤¾ð═Â╔┤¼╩«ÂÓ╦Êú¼═¨ÀÁË┌░Î╔│íó▓¦╬▓íó╚¹▓¿íóÛû┴_Á╚ÁÏú¼├Ô┘M×Ú├±▒èÀ■äıíúÎÈ┤╦ú¼║■à^(q¿▒)Á─╚╦├±─¤üÝ▒▒═¨ú¼╚╦Ïø░▓╚½ú¼©─îæ┴╦Òõ¢¡╦«┬À▀\¦ö?sh¿┤)─Üv╩Àú¼╦¹▒¥╚╦Ê▓ÎuØMÂ┤═Ñíú
1912─Ûú¼©]╔┘─¤╚Ñ╩└║¾ú¼┴xÂ╔┐é¥ÍÈ┌╔Å╗¿╠┴Á─┤¾À╠├È÷ÈO┴╦í░©]╣½╔┘─¤┼ã╬╗í▒ú¼│ú─Û¤Ò╗▓╗öÓíú┼ã╬╗â╔é╚▀ÇËð─¥┐╠îª┬ô(li¿ón)ú║í░─¤Â╔▒▒ú¼▒▒Â╔─¤ú¼Â╔─¤Â╔▒▒ú¼─¤▒▒ÄÎòr═¼Ê╗Â╔íúç°æn├±ú¼├±ænç°ú¼ænç°æn├±ú¼ç°├±║╬╚ı├ÔÍÏæníúí▒
×Ú╝o─¯▀@╬╗©]└¤¤╚╚╦ú¼ð┬¢ÍÁ─©]╝Ê└¤╬¦Í┴¢±ÊÓ▒ú┤µ═Û║├ú¼2007─Ûú¼▒╗Òõ¢¡╩ð╣½▓╝×Ú╩ð╝ë╬─╬´▒úÎoå╬╬╗íú©]╝ÊÈ┌ð┬¢Í║¾╚╦¦à│÷íúí░╬─©´í▒òrú¼×Ú║å╗»ØhÎÍú¼©]ðıÂÓ©─×ÚÂ┼ðı┴╦íú
¢ÔÀ┼║¾ú¼╚╦├±ı■©«ÅU│²┴╦▒ú╝ÎÍãú¼│╔┴ó┴╦ð┬¢Í¥Ë╬»ò■íú▓óîó¢ÍÁ└╣▄¦áÀÂç·öU┤¾ú¼═¨─¤Á¢┴╦ù¸ÿõÒÔú¼═¨û|Á¢┴╦¤┬¡éÿ‗íú1956─Ûú¼╚½┐h╣ñ╔╠ÿI(y¿¿)╔þò■͸┴x©─Èýú¼Î▀║¤Î¸╗»Á└┬Àíú1958─Û┤¾▄S▀Mú¼¡é║■µé(zh¿¿n)ı■©«È┌ð┬¢Í¤╚║¾Ìkã┴╦▒Ì┼┌ÅSíó╗»╣ñÅSíó╝ê¤õÅSíó┤u═▀ÅSíó▓ú┴ºÅSíóãñ╝■ÅSÁ╚µé(zh¿¿n)Ìkã¾ÿI(y¿¿)ú¼░▓Í├┴╦┤¾┼·¥Ë├±¥═ÿI(y¿¿)íú
─Ãòr│÷¼F(xi¿ñn)┴╦â╔éÇ┼«Åè╚╦ú║Ê╗éÇ╩Ã╗»╣ñÅSÅSÚL▓╠ÿÀ▒°ú¼Ê╗éÇ╩Ã▓ú┴ºÅSÅSÚL╣¨À³╠mú¼╦²éâ?y¿¡u)Ú░l(f¿í)ı╣¢ÍÌkã¾ÿI(y¿¿)ú¼Èý©ú¢ÍÁ└¥Ë├±Î¸┴╦┤¾Ïò½IíúÁ¢╚þ¢±▀ÇËð╚╦È┌╠ßã╦²éâíúÊ▓┐╔Êèú¼├½Í¸¤»1955─Û╠ß│÷Á─í░ïD┼«─▄Ýö░Ù▀à╠ýí▒ú¼╩Ãıµı²Á─ãı╩└ârÍÁúí
ð┬¢ÍËðÍ°Ëã¥├Á─├Ì┬Úíó©╠Ú┘¢╗ÊÎÜv╩Àú¼┐hı■©«È┌┤╦¢¿┴ó┴╦ç°áI├Ì┬Ú╣½╦¥íóÚ¬¢█Ìkíóê@╦çê÷íóÒõ¢¡┬Ú╝ÅÅSÁ╚ã¾ÿI(y¿¿)ú¼┴Ý═Ô▀ÇËð┐h╚Ô╩│╦««a(ch¿ún)╣½╦¥íóà^(q¿▒)ðl(w¿¿i)╔·È║íóâªð¯╦¨íóù¸ÿõÒÔ╣®õN╔þíó╚Ô╩│ı¥Á╚íú╬¶╚ıÙu╣½Îý╔¤Á─³S│■▓┼ú¼├±ç°òr×Ú┐hı■©«┐ãåTú¼╦¹╝ÊÁ─└¤─¥╬¦▒╗ı■©«ı¸Ë├║¾ú¼©─│╔┴╦ÞTÈýÅSú¼║¾ËÍ©─×ÚÒõ¢¡Á┌Ê╗ÖCðÁÅSú¼¼F(xi¿ñn)╚þ¢±│╔┴╦║■─¤îúË├ã¹▄çÍãÈýÅSú¼×ÚÍð┬ô(li¿ón)ÍÏ┐ãÁ─╣╔Ù┼ã¾ÿI(y¿¿)íú
ç°├±Á┌╬Õ╦¢┴óðíîW║═┬Ö╝ÊÎ┌ý¶║¤│╔┴╦¶ö?sh¿┤)Ê║■ðíîWú¼║¾©─├¹ä┘└¹ðíîWíú║óÎËéâ┤®╦¾Ë┌ð┬¢Íú¼│¬©Þ╠°╬Þíó╠°└Kíó╠°ððÎËú¼▀Ç┼¥╝ê┼┌íóØLÞF¡h(hu¿ón)íóÁ°ÅùÎËú¼ƒß¶[ÀÃ│úíú
▀M╚Ù╔¤╩└╝o░╦╩«─Û┤·ú¼ð┬¢ÍÍÏð─¤‗Òõ¢¡╩ðÍðð─ÌDÊãú¼▀@└´│²▒ú┤µ┴╦Ê╗éÇ─¤ÏøÁÛíóÊ╗éÇ░┘ÏøÁÛíóÊ╗éÇ├µ^═Ôú¼ãõ╦³ÊÐ▓╗Å═┤µÈ┌íúÐÏ¢ÍÁ─├±À┐ú¼Ê▓¢³║§░ÙöÁ(sh¿┤)╩Ã┐ıÁ─íúËð³c¤±▓▄ЮÃ█ð╬╚¦┘Z©«ú¼í░╚þ¢±═Ô├µÁ─╝▄ÎËÙm╬┤╔§Á╣ú¼â╚(n¿¿i)─ÊàsÊ▓▒M╔¤üÝ┴╦í▒íú
¤±╗Ï╣ÔÀÁıı╦ãÁ─ú¼─│╠ýú¼▀@└´═╗╚╗│÷┴╦éÇ┼«├¹╚╦ú¼ðıäóú¼ıfÎÈ╝║ë¶Á¢í░┤¸╣½©¢¾wí▒ú¼▒Ò╚í┴╦éÇÀ¿├¹¢ðí░┤¸╣½Á¨Á¨í▒ú¼╦²ÊÈ│¼À▓Á─ÍÃ╗█║═╚þ╗╔Á─┐┌╔Óú¼Ë├╠ý¤┬╚╦Â╝▓╗«Á─í░╚íöÁ(sh¿┤)í▒í░╦ÒÏÈí▒Á╚À¢À¿ú¼×Ú╚║▒è┐┤▓íú¼ı{(di¿ño)└Ý╗╝ı▀Á─ð─└Ýú¼¥╣╔¯Á├├±▒è¤▓É█íú│┴╝┼┴╦ÂÓòrÁ─ð┬¢ÍËÍ├¹┬ò┤¾ı±ú¼ÚT═Ñ╚¶╩ðú¼À¢êAöÁ(sh¿┤)░┘└´ú¼üÝıÊí░┤¸╣½Á¨Á¨í▒┐┤▓íÁ─ú¼╚þ▀^¢¡Í«÷aíú
╚þ¢±Á─ð┬¢ÍТú¼╦«─Ó┬À┤·╠µ┴╦┬Ú╩»┬Àú¼└¤Í±─¥╬¦ÚgÙsÍ°ð┬ðÌÁ─┤u═▀╬¦ú¼Á¢╠Ä╩ÃÜêȽöÓ▒┌ú¼Üv╩ÀÁ─║██E¬q┤µíú¼F(xi¿ñn)È┌ú¼ð┬¢ÍÈ┌ððı■╔¤ÊÐ▓ó╚Ù┴╦ð┬┼d╔þà^(q¿▒)íúÊ‗│Ã╩ð¢¿ÈO╬¸Êãú¼═¨╚ıð·ç╠Á─ð┬¢ÍÒU╚A═╩▒Mú¼ð┬¢ÍÁ─║¾╚╦¤‗═¨ð┬Á─╔·╗¯ú¼╝è╝è░ß▀wÁ¢┴╦╩ðÍðð─íú
ð┬¢Í┤╣┤╣└¤ÊËú¼Á½╚ÈËðÈSÂÓ└¤╚╦┴¶æ┘▀@ùl¢Í¤´ú¼╦¹éâ¥▄¢^â║┼«Á─ʬþú¼êÈ¿ÁÏ┴¶╩ÏÈ┌ÎÈ╝║Á─└¤╬¦└´íú╠ýÜÔ║├Á─òr║‗ú¼╩▓├┤└¯Á¨Ð¢ú¼äóÁ¨Ð¢ú¼©]èÍÜ▓Тú¼òr▓╗òr▀ÇͨͰ╣ıı╚ú¼▀╦íó▀╦íó▀╦ÁÏÃ├┤‗Í°╦«─Ó┬À├µú¼¤Ó╗ÑÎ▀Î▀ú¼╗‗│÷üÝò±╠½Ûûíú╣ıı╚Á─ËÓʶÙmø]┬Ú╩»¢Í─ÃÿËÃÕ┤Óú¼Á½Ê▓─▄é¸╚Ñ║├▀hú¼║├▀hí¡í¡
θı▀║å¢Úú║
Åê▀B¤▓ú¼Òõ¢¡╩ðθ╝Êàf(xi¿ª)ò■©▒͸¤» ú¼Òõ¢¡╩ð├±Úg╬─╦ç╝Êàf(xi¿ª)ò■©▒͸¤»íú
©Á└‗└‗ú¼Òõ¢¡╩ðθ╝Êàf(xi¿ª)ò■©▒͸¤»ú¼Òõ¢¡╩ð├±Úg╬─╦ç╝Êàf(xi¿ª)ò■©▒͸¤»ú¼Òõ¢¡╩ð┼«Î¸╝Êàf(xi¿ª)ò■©▒͸¤»íú
σ¥Äú║˸║ã îÅ©Õú║³S║ã